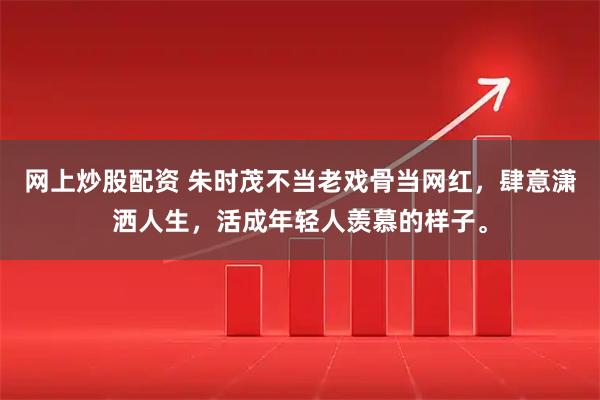说到历史性的变化,天道日月网上炒股配资,运行不息。其实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。
我出生于1952年,几乎经历我们这个国家所有的困难时期,我对那个时代的感受最为深切。
所以我认为是改革开放救了中国,救了我们这个国家。
我认为改革开放是一件特别大的不得了事情,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。一切问题都可以坐下来讨论,唯独能把吃饭问题解决了,就是天下一等好事,千古变革的大事。
从我出生有记忆的年月起,榆林人的吃食就一直非常的困难。要说关于饭店的记忆,这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了。在我小的时候榆林街道上只有很小的饭铺,名叫工农食堂或国营食堂,也没什么店铺,卖的最好的饭,就是粉汤、素烩菜和玉米馍。
要说吃得最好的在我的记忆中,就是我大姐出嫁时,吃过一顿杂烩菜,就是榆林人说的连毛杂烩,让我终生难忘。
何志铭的姐姐和妹妹们编辑
展开剩余92%说到老榆林十二件、拼三鲜、吃席、豆腐宴、羊道,这都是1978年以后的事情了。所以,我过去忧心忡忡,那时候好多东西被毁灭了,觉得特别的痛心。其实人的再生能力特别强,如今有些又都挖掘恢复了,真是没有做不到,只有想不到。
在我的记忆里,饥饿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童年,国家困难时期。路遥有一篇小说,《在困难的日子里》,他把农村的困难应该说写得很充分。后来他常对人说:“人到什么时候,能够想吃什么就吃什么?该多好啊。”对饥饿的记忆路遥写得最真切。
何志铭(左二)与路遥的父亲、母亲、妹妹 1993年10月编辑
我们家虽然是榆林的城市居民,但也好不到哪去。街道办的公共食堂,虽然是用了我们家的房子,仍然吃饭要交费。我们交不起饭钱时候,最多曾有三天都没有吃过饭,三天没有吃过饭,现在人能体会一下,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?
父亲心疼,看着我是男孩子,偷偷的把我带到街上,用身上唯一的两毛钱,给我买了一碗粉浆饭。当时不让自己在家里做饭,半夜的时候一家人偷偷的把窗户堵住,在锅里煮一点自己挖回的白菜根吃。公共食堂买回的一盆稀饭,一会儿就让娃娃们抢光了,我妈只能喝涮锅水。
我的母亲编辑
那些公共食堂的管理员们,吃得红光满面。导致了我一生厌恶这些管理员的平庸之恶,包括后来我在西影食堂帮厨,也是这样的感觉。
那时候,城市居民都吃得供应粮,每人平均28斤。每月买粮食要起很早去排队,粗粮很多,细粮很少。因为种类多,所以要拿大大小小、许许多多的口袋,用钱来买粮。
因为网上炒股配资人普遍营养不良饭量大,粮食半月就吃完。
没办法就去城外庄稼地里,在农民收获过的土地里,偷偷去刨蔓蔓(土豆),偶尔能够刨到一两个蔓蔓那种欣喜之状,至今难忘。
可是有好几次我刚得到一点蔓蔓,在返家走的路上,却遭到看地人的追打,用柳条抽打我,并且踩碎了我的筐子,我坐在地上放声哭。
过去,我们家有10口人就得有十缸酸白菜。要从今年的秋冬吃到到第二年的春夏。现在,这些大黑瓷缸都退休了,从农村到城市,那些烂房子里到处扔着老瓷缸。那些收购老物件的人,高兴坏了。
那时候,人饿得不行,从乡下亲戚家要了糠,吃糠后拉不下来,七八岁的我,让奶奶用大竖柜上铜钥匙往出勾,捅着我疼得放声哭。
我的祖母编辑
家贫,我九岁才上小学,穿着我妈妈在胳膊肘上补羊皮的黑棉袄,跑在贾盘石上巷第四完小念书。
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悄悄地告诉我说:最近农贸市场又放开啦!他高兴地让我们都笑了。但是时间不长,他又告诉说农贸市场又关了,挣钱和吃饭又麻烦了。
1963年,我最小的弟弟出生,家里实在没有粮吃,趁着父亲不在家,我母亲用二升小米,把我弟弟换给了乡下人,父亲回家知道这个事情,二话没说追去了。连夜把我弟弟抱回来了。据榆林老人说,抱回来了孩子,一般都很难养活。我的小弟后来活了40多岁就走了。
我的小弟编辑
1964年,我爷爷去世了,在入殓的时候,我看到有人把我爷爷的寿衣、被褥,剪破,再倒上菜油。后来我问父亲才知道,这是生怕盗墓贼盗取寿衣转手再卖。
我的袓父编辑
乡下舅舅在村里河畔上采集了蒲毛,装在褡裢里卖给城里人壮枕头。总被人说成是坏分子,挨斗。
一天,舅舅在街上,遇见了我姐,他向我姐姐要五分钱,我姐姐当时不好意思,身上也没有零钱,没给。不久舅舅去世了。姐姐想起这就心痛不已。
后来,舅母一家人饿的不行了,在生产队又开个介绍信,一家人拖儿带女地向内蒙古方向流浪,最后落户在地广人稀的巴彦淖尔盟。
如今,我常常路过我岳母家巷子,看着垃圾桶内倒的豆腐渣,冒着热气,我发呆,在过去,有点关系的人家才能挖到一点豆渣。
1966年,我14岁,小学毕业。要上中学时,家里拿不出三块钱的学费,我从此辍学。
何志铭少年时代 1967年编辑
一九六七年夏秋之际,榆林群众组织开打,我是个饥饿的小孩,给他们帮忙,为混的能喝碗稀饭,吃上一个平时没见过的白馍。两帮人在县招待所撕打时,我特别的好奇,那一天,我从刚塌了招待所南墙的破洞里偷偷地钻进去院子。一看,原来正是招待所的大灶房内。我再仔细一看,居然有一大锅烩菜,正冒着蒸腾的热气,但是,上面漂浮了一层房顶上塌下来的土渣。锅台上还有许多用弹弓打进来的滚珠铁螺钉。我觉得多么可惜了一大锅烩菜啊!显然他们正准备吃这近百人的一大锅烩菜时,仓皇逃跑了,我看着这一大锅菜,嘴里无奈地嚥下了口水……
多少年后,我坐在西安家里的餐桌前,想起这一锅烩菜,不由自己悄悄地抹泪,妻子问我:“你咋了?你咋啦?”我摇摇头说:“没什么!”我什么都没说。
1971年9月,西影招工是去食堂当伙夫,我心一撗想,还是先把肚子吃饱了再说,那年我十九岁。
何志铭西安电影制片厂工作前,离开榆林时所摄1971.9.编辑
人青春期的身体和体质,往往决定了人的性格和命运,包括后来的疾病健康等等。吃、住、行,都是要人命的大事,对于国家来说才是真正的大器。老百姓就是靠这些活命,人民活好了,一个国家才有希望。
在榆林瓦窑沟巷出生地留影编辑
我们家开始在榆林城老街后边,瓦窑沟上巷。后来逐渐向南移到后水圪坨上巷,最后1965年春天,我二叔和三叔分别从横山、鱼河搬家回到榆林,我父亲是老大,只好把水圪坨上巷三间南房让给了他们,我家挪到了定惠寺上巷18号院,我舅爷的破房里。
现在,偶尔路过时,我也会绕着去凭吊一下老地方,如此,全坍塌几乎夷为平地,我徘徊在砖块瓦砾中,忧思难忘。
何志铭在榆林定慧寺十八号住过的旧址编辑
那时候,家里将近10口人,就住在两间大约30平方的房子里,一到下雨天,房子就漏水,地下也没有砖全是坑,家里面还打着伞,放着大盆小盆儿在接水。
榆林人住的很像北京大杂院,大门一般在东南方向,厕所就在西南角,百十来口人,所有的污水也都倒入大茅坑,娃娃们一不小心就掉进去了。
住的问题和人口有极大关系。五十年代,政府鼓励产生生育,到七十年代,二十年后进入成人期,要成家生子,于是人口爆涨,榆林人开始向四合院下手,家家在四合院里盖小房,老房门窗大改全部移到房檐下。又加上防修备战,挖战壕,地下再挖防空洞,地面盖小房,家家拉砖,榆林的四合院基本毁于这个时期。
榆林远离省城,交通和出行问题,一直就是一个大难题。
我小的时候,地方百废俱兴,从南门出去的南大道,似乎年年都在修路,在我的印象里,总是从坟墓的群里穿过。公路边的水壕里,就有掉下来的是的死人骨头、骷髅。抬头望崖上有半截朽木棺材板,吓得我们这些小孩,很是恐惧。
在我父亲那个年代,常听他说到西安、铜川送马上火车,要步走十八天的大马站,也就是说有18个古代驿站,从榆林到铜川的路途,然后上火车把马转送到外地。
过去人全靠步行,坐不起车,靠着背、扛、挑。我父亲去内蒙打工,都是挑一担行李,我送他一直到城北,过了镇北台的谢家坬。
我辍学后,跟着父亲打工,学会了提泥包和糊仰尘(顶棚)。我是我们家弟兄中和我父亲相处,干活时间最长的。
我和我父亲当小工远去了巴拉素,那一次工地赔钱了,父亲和我半夜偷着往榆林跑。当天黑时到了泡驴坬,照见城中灯火时,却黑的看不见路,只好当晚蹲在烫人的火炕上,䓁到天亮才回家。
十七岁那年我在响水下了车,然后跟着父亲背毡卷,去横山的高镇当小工。从那一次,我才知道一个人一天能走多少里路?
何志铭在导演纪录片《李鼎铭先生》时编辑
从榆林到鱼河堡八十里,就是一人一天正常的步行的距离。可我们去这高镇的路,一天走到120里路,我的脚腿都肿了。我不停的问父亲到了没?父亲总说一句话:“翻过这个山就到了!”只是过了几座山再问,父亲仍然是这样说着,”“马上就到了!”
当天晚上歇在韩岔车马店,我腿肿的无法入睡,整个一个晚上听着水磨边跌水哗哗地响了一夜,借着灶火口的火光,听一个同炕的腿跛的放羊人讲他,参加兰州战役激战受伤流血的故事。
出这一次远门后,我才真正的算长大了,知道活人的不易,再也不留恋少年时代手里玩得那些棍棒了。离开榆林才真正懂得榆林,我十九岁离榆林,乡愁萦绕了我的多半生。
何志铭在最后离榆林时院子门口留影编辑
一九七一年参加工作到西安,要坐三天汽车,还需在铜川上火车才能到西安。
刚开始不让回家过年,能到让回家过年时,往往又大雪封路,连车票买不到,我只好赶到了咸阳去,上了火车连个缝都没有,我只好垂头丧气又回到西安。
那时候,没有西安直通榆林的车,只好坐火车要绕到山西介休后,连夜再坐卡车到绥德转车回榆林。那一段正是吕梁山最冷的寒冬雪夜,到绥德下车时,人脚腿冻僵,弯得打不直了,俩人架着胳膊双脚才落地。回家一进门腮帮冻得连话都说不成了,捂着脸,一挥手就爬上了热炕锅头,先往过来暖人要紧。
在过去那个年代,很难想象有一天个人会有汽车,我结婚的年代就推着几辆自行车,都觉得很牛很牛了。我常想,过去我都不知自己丢了多少辆自行车了。
现在,我常看到街边的共享自行车,一排排地倒在风雨中,都没人理……
何志铭在雪天拍片编辑
过去榆林属于高寒地区,冬天非常漫长,春天不停地刮风,刮的门窗如烂鼓敲响,风沙把人刮的眼睛难睁开,许多人得了沙眼病。
直到现在,我还常在梦中听见小时候风刮窗户“啪啪”响地的声音。
上学娃娃们手背手指都冻烂,红肿化脓流黄水。为了取暖孩子们一下课就相互撕打着取暖。
一双老毡窝子编辑
有的人穿着沉重的毡窝子,耳朵上还戴兔尾巴圈防冻。
榆林城娃娃们无论贫富,都有这样的事情,从青云山煤矿,秦庄梁煤矿,也叫人民煤矿拾煤渣的经历,从这年秋冬到第二年秋冬,要够一家十多口人的做饭和取暖用煤,每次背五六十斤, 从我姐姐到我,我大妹,我们三人都拾过煤渣。
冬天娃娃们衣衫褴褛,风和煤沙灰土扑在脸上,鼻孔下全是黑的,个个形同叫化子一样。
何志铭 拍摄 1986年榆林芹河附近的孩子们编辑
那时候秦庄梁煤炭地势高,向榆林城望去,万家屋顶,冒着煤烟,天上全是一层厚厚地黑云,云里又传来一阵阵嗡嗡地响的鸽哨声。
那时候家里洗澡条件不具备,娃娃大人身上都有虱子。加上吃得又不行,小孩总有蛔虫总闹肚子。
过去榆林城是半城工匠半城商,工地很少、要有关系才能上工干活,商业更不行。我妈常说:有屁股还没有挨打处!
我的母亲编辑
我的父亲编辑
但是,富忧愁,穷乐活。穷且愈坚,无论生活何等艰难,人们依然是报之以歌。艰难的历程,伟大的变迁。
新中国成立75周年,改革开放40年。个人命运,其实是国家命运。
改革开放解决了劳动自由、流动自由、私人财产受保护,个人可以成为企业家,有财产继承权。企业家可以入党,进人大、政协,在政治获得了新生。
现在时代最大好处,是把个人价值全体现足了,社会相对公平。再者就是文化成为一切事业的支撑力量。
但是,我们还是要记住这句话: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,就是人们从没从历史中吸取过教训。
因为,只有不断地反思历史,我们的国家人民才可能进步。
发布于:陕西省配资官方开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